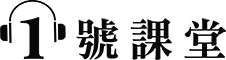這一集,我們要為大家打開《史記》中的第三個智慧錦囊,那就是:把事情做對,更要做對的事。
歷史雖是過往人物的行跡,只要經過現代精神的細心觀照和轉化,它也能成為現代人的寶貴資產。我在為年輕朋友編寫《史記》的讀本時,總試著用各種現代學科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的核心問題,不是只把古文翻成白話文而已,其中受管理學的啟發頗多。
福原義春是日本著名企業資生堂的名譽會長,對該公司的貢獻很大。他最喜歡的一部書就是《史記》,並且認為《史記》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經營管理。2008年,有一期的《天下雜誌》就這個問題訪問了他。福原義春答說:「人生會累積許多經驗,愈來愈會發現,許多成功與失敗的模式是類似的,把歷史縱深拉到一千多年前的《史記》,當時的人已經經歷過各式各樣的人生經驗,在其中累積智慧與教訓,而且在現代依然適用,這些都是免費學習古人的智慧。由古鑑今,可以從《史記》汲取古人的智慧,讓自己避免重蹈覆轍,得到許多收穫。」福原義春的這番說法不乏「以史為鑑,可以知興替」的傳統色彩,但是能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讀《史記》,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。福原義春還建議有志成為領導人的年輕人,都要讀讀《史記》。
怎麼用管理學的觀點來讀《史記》呢?這裡,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說吧!
遠在堯舜的時期,洪水氾濫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。有一次,堯問大臣和諸侯:「你們知道有誰能治大水?」大臣和諸侯都推薦了鯀。堯對鯀這個人還算了解,說:「鯀經常不聽從命令,都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做事,以致拖累同伴。他行嗎?」大臣和諸侯說:「在治水這方面,目前沒有人比他更厲害。要不,您試試?」既然大家都這麼說,堯也只好用鯀來治水。
鯀治大水,採用的是圍堵的方法,哪裡有氾濫,就在哪裡築堤。這麼埋頭苦幹,九年過去,沒有半點成績,洪水的問題越發嚴重,而百姓的生活更加不方便。
當時,堯的接班人舜正代替天子處理國政,到四方去巡視。在巡行的途中,舜看到鯀治水,越治越糟,實在太不像話,便行使代理天子的權力,在羽山這個地方將鯀處死。有人問:「鯀已經處死,接下來要叫誰接他的工作呢?」舜的回答是:「讓禹來做吧!」
禹是鯀的兒子。他治大水,不用圍堵的方法,而是用疏導的辦法。也就是說,多開些渠道,讓大水有流動的去處。這麼治了十三年,終於把洪水氾濫的問題解決了。藉由治水的工作,禹重新畫定了九州的邊界,讓國土獲得一次重要的整頓。
禹治水的功績十分偉大。後來,舜就把帝位讓給了他,而人民都尊稱禹為大禹。
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,鯀的失敗,歸因於他僅僅把事情做對,卻沒有做出對的事情。而大禹的成功,是他既做出對的事情,又把事情做對。
什麼才是該做的事,這是屬於決策方面的問題,在開始的時候就得好好考慮。怎麼做才能讓事情順利完成,這是屬於執行方面的問題,是在過程中要留意的。決策一旦出現錯誤,就算執行得再認真,也只是多做多錯。就像鯀治水,採用圍堵的錯誤決策,努力了九年,換來的是洪水問題的惡化,而他也為此付出了性命。
現代管理學之父,彼得․杜拉克,非常重視「效率」和「效能」這兩個詞的區分。效率所關切的是「怎麼把事情做對」,要的是工作品質的優化。效能所關切的是「怎麼做出對的事情」,要的是工作目標的正確,以及工作結果的效益。杜拉克說:「最有效率的企業,如果它的效率用在錯誤的地方──也就是缺乏效能──即使效率再驚人,也難以成事,更別說是成功。」如果把鯀的治水團隊比作一個水利工程的企業,那麼杜拉克的這些話,不就為這個企業的失敗做了最好的註腳?
我們讀《史記》,可以發現很多人都犯了這方面的錯誤,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。例如漢武帝,當時就不應該為了求取汗血馬而向大宛國發動軍事攻擊。這個決策是個非常冒險的決策。大宛國遠在西域,距離太過遙遠,補給線拉得太長,肯定會出問題。何況當時漢朝又跟匈奴在打仗,多有折損。許多大臣都勸漢武帝專心對付匈奴,不要分散兵力。但是漢武帝很固執,就是不聽,還說:「連個小小的大宛國都打不下來,那麼,以後那些西域的國家不是會瞧不起我大漢帝國嗎?」
漢武帝一共花了四年來打大宛國,仗是打贏了,汗血馬也求到了,但損失了十多萬人的性命,以及無法估算的金錢花費。坦白說,如此勞民傷財,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。
把事情做對,更要做對的事。在管理學的領域裡,這個原則只能算是一個基本的觀念,一點都不難懂。可是當我們觀察歷史上那些影響深遠的事件時,你會發現當時的決策者所缺乏的,往往就是這個基本觀念。
越是基本的東西,越容易遭到忽視。別說古代的決策者是這樣,現代的決策者也不一定好到哪裡去。就拿台灣一例一休的政策來說,決策者的原意是要讓勞工正常休假,若有加班的情形,可以多拿點加班費。但是決策者忽略了許多行業有它們自己的工作生態和特性。不講彈性而把所有的行業統統納在一個框架來約束,當然惹得怨聲四起。至於一般的勞工,收入並沒有增加,反而因為無班可加而減少。企業的人力成本增加了,一定會反映在消費者身上,物價因此跟著上揚起來;荷包淺一點的民眾過起日子,也就更辛苦了。請問,決策者原本的美意這時候還看得到嗎?
這段施政的經歷,終究會成為歷史。要是以後有人也像我們用管理學的基本觀念來分析《史記》的事例,他們會怎麼評判這段歷史呢?我想,他們應該會這麼說:當初,政府在推這個政策時,非常具有「效率」,很快就讓立法院通過法案,很快也公布了;但是從結果來看,它絕對是個缺乏「效能」的政策,因為決策者一開始就沒有做出對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