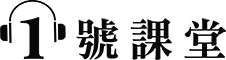Hi我是蔡佳妤,現在,想和你分享我的故事…。
記得家母曾跟我說段往事:當年她在醫院生我,孩子那洪亮的哭聲,像個天生的總司令。醫生興奮跑來向我阿嬤道喜:「她有那兩顆啊!」我阿嬤聽了多得意,朝親友說:「兒子!生了兒子!」孰不知醫生講的是兩顆酒窩。
往後的童年,我就靠這兩塊臉部凹陷活著。逢年過節大人都喜歡逗弄孩子,我的笑容開始有了娛樂作用,他們偏愛拿手往人臉頰鑽,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,有句俗語說吃飽撐著。後來我安慰自己─這也算是種福氣,你一笑便有紅包拿,還有糖可吃。
那時候,我不覺得自己跟別人有什麼不同。我媽知道這孩子愛笑,天性親近,但身上老是瘀青,於是只往「被欺負」那方面猜想,從未想過我視力直落0.01。檢查那日可能病人看得多,醫生沒耐心,當場就說:「妳這孩子根本近乎全盲。」母親看我在身旁,壓住心慌速速回他:「這很正常。人會長高,視力也一樣。」
接下來10 多年,我媽都當她在寫科幻小說。她編了無數奇葩故事,說明人類眼珠子上的白膜,會因為書讀得越多,越能漸漸把世間百態看清楚。編到一半還轉往武俠線路,說人若想看清楚,多半要付出些代價,往後面對正義,你不能明明看到,卻當作沒有看見。
因為幾乎沒有視力,我無法辨知一個女人,將生命裡最美的歲月,獻給近乎失明的女兒,她究竟被剝奪了什麼? 我聽過一夜蒼老十歲的傳聞,也聽說我未能看見,她也難以闔眼。可如果這宇宙真有所謂上帝視角,你會看見我母親從一名芭蕾舞者,剃了光頭,增胖20 公斤,變成了計程車司機;因為她清楚唯有母兼父職,才能保護她自己,也才能保護嗷嗷待哺的孩子。
無數漫熬長夜,她為了避免母女雙雙被恐懼吞噬、被憂患在心口鑿出某種無以言喻也難以痊癒的傷痕,她將自己化為曙光,於是才有那《一千零一夜》,才有那些說來我深信不疑的故事,也才有那溫情、仁慈與光明,倒影在我一片霧茫的視網膜上,留下希望。這時候我還不知,自己未來將有機會去看見美好,去看見盛夏的藍天白雲,還有曾經被母親帶到一個地方,只說了句「今天天氣很好」,便感到輕如羽毛的溫暖,聞到衣服晒來的淡香,從此知道一個名字喚作太陽的好東西。
20 年風雨飄搖的日子,我和母親相互依偎。她發了狂似地積攢收入,從北到南送貨打零工,從臺灣將女兒送去日本;許是她說的故事感動了誰,許是她不知哪來的膽量遠走異鄉,她如願找到了良醫,願意一步步治好孩子的眼睛。
只不過,治療過程是十分漫長,也足以散盡家財的。在我的記憶中,母親把「看醫生」包裝成「私人旅遊」。我媽會爬梳深度文化景點,會細心安排路程,會讓醫院作為東京迪士尼的轉運站,毫無嘶吼痛哭與掙扎,我還穿上點點洋裝,胸口挺著一隻米老鼠,在不同院區張揚過街。看完醫生,她通常會帶我去大吃一頓。因為她心事深,老覺得沒把孩子生好,那起碼要讓她吃好。我對醫生與廚師因此有了莫名好感,他們都是白衣人士,他們都懂得如何拿起刀,他們手裡有時候也都會出現酒精的味道。
母親年年捉襟見肘,帶我展開冒險的就醫之旅,也有窮途末路的時候;我們曾住過滿屋蟑螂的房子,她不用欺瞞我,反正我也看不見。我們曾窩在一塊吃同碗拉麵,她捨下自個兒那份,給孩子加點愛吃的玉米,誰曉得那次我掉牙,忙著找牙齒的母親,終歸餓了肚子。還有小時候,我總期待搭電車到大阪的難波站,誰叫我們母女倆都愛搜刮高島屋7點後的出清美食。在前幾站,我就會拉起母親衣角問:「媽媽,下一站我們要去哪裡?」
長大後,我才明白對母親而言,孩子的幸福與笑容就是她的下一站。許許多多,這樣又甜蜜又拮据的回憶,深深烙印在我視覺逐漸清晰的日子,癒合我們心底潰瘍的傷口。說起來,我沒有什麼突然痊癒、大驚大喜的剎那,我一直都很相信我媽,她堅信女兒終究會重見光明這事,這宇宙自然也隨了她。
仔細認真想,倒是27歲那年在臺灣進行的最後一場手術,帶來的感觸較多。在此之前,日本醫生說能治好真是奇蹟,視力從0.01 已經來到1.0,剩餘的是外觀與眼部肌肉問題,俗稱「鬥雞眼」。說實話,我等這天很久了。因為肌肉緊繃導致偏頭痛不斷,因為複視影響學習歷程特別困難。這些都是旁人無從體會的過程,更別說面對暗戀對象和職業生涯,每回我都在追求所愛之時,打退堂鼓。
後來,輾轉從日本回到臺灣,負責我斜視手術的是蔡紫薰醫師。她是那種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」,掌舵穩得出奇卻不傲慢的性子。在手術之後,我們用回診方式記錄心得,她也不斷想了解斜視病患,真正的身心痛楚、人際障礙與生活困難。很快地就到了手術前一天,我赴醫院報到,詳實做了健康檢查,麻醉師詢問飲酒經歷,蔡醫師過來在我左眼標記開刀位置,我自始至終不毛躁,乖得像條燙平的領帶。
睡醒隔天,我老早在病房等待,心想這濃密睫毛底下的光學結構,終於來到原廠維修之日。幾度我望向鏡子,想記住眼睛歪斜的程度。我都快忘記有多少年了,我不斷對著鏡子,確認要笑得多燦爛、採取何種角度面對人群,才不會被看出來。
我又再次望向門廊。母親大包小包走進來,老樣子開始聊今晚要吃什麼,她似乎察覺到這是我們人生共同的轉折點,她盼望在這時候,說些能讓我永遠記住她的事情,說來說去都跟食物有關。很顯然地,我們的母女關係,很大部分建立在吃這件事,由香味、味蕾、聽覺織就的親密交纏,幾乎是摒除視覺地,描摹出這個世界的感官風景。
三番兩次,聽見輪子聲,以為是護士推了手術床過來,她就會立刻停下,而我整個人卻像在賽道旁都要尖叫起來,跑出去一看,又發現時候未到,默默地退回來待在床邊,她接續著講,我靜靜的聽,突然覺得《一千零一夜》算什麼,母親到了這天說了近一萬夜。終於,手術床被推了進來,我簡直欣喜若狂跳上去,母親臉倒臭得像孩子要被送進屠宰場。我口口聲聲安慰母親,身上卻佈滿興奮高昂、群起站立的顆粒;就像一群背主的逆賊一樣。
來到手術室,又是同樣的親切感。作為白衣人士的共同場域,此刻我像是一塊會呼吸的肉。這氣溫讓人如此清醒,我情緒又如此亢奮,不免胡思亂想,是否會發生麻醉失效、人醒著開刀的慘境。在此真心建議大家開刀前沒事別Google,我講真的。哪知護士一句「放鬆,我要讓妳睡了喔!」,呼吸器罩上來,我一下遁入夢境。
這場手術,你說有多麼重獲新生、喜極而泣的感觸,沒有,遠遠沒有我想像得那麼多。倒是這一秒中浮上心頭的是,我明明白白知道,從此往後,我再也沒有非得回到醫院的理由。可是,我卻不想從和母親的這段回憶裡出走。
對一個孩子來說,童年的餐桌底下總是充滿樂趣與秘密。開飯時,我跟母親之間有句暗號:「來鋪張報紙吧。」據說這暗號是老爸留下來,他最拿手的料理是瓜仔雞湯,我最後一次喝到它,是在我媽肚裡。每當我聽見這聲呼喚,便會爬上座椅,一雙小腳丫在那騰空晃啊晃,等吃飯,聽著母親在那翻閱老半天,拿起重物壓在報紙兩角,飯碗端來,筷具擺上,酸菜扣肉混著印刷墨味,我聞著、吃著長大。
說起來,我媽是我們家少數擅於烹火之人,這讓她成為充滿創造力的女性。詩書中琴棋書畫皆通的才女,大概在說她。但在我看來,這些都是被現實賞耳光之後,被生活給磨礪出來的。
她來自玉里山鎮,從小排行老二。她的命就像老房二樓般,排水、糞管都從這經過,就是沒好處流過;她憑著軍家兒女的生活經驗,7 歲學會生火,9 歲便能補鞋,打小照顧病弱體虛的姐姐,還得帶上兩個妹妹。那時,窮人家生活基本按照戰時在過,豬油撿人家用剩的做成肥皂,水溝摸魚抓蝦去跟人換菜。所幸她樂觀,日子也就過去了。童年日子雖苦,但我媽活得一點都不將就。她有套黑旗袍,自個兒湊珠子,憑熟悉身架子穿針引線做出來,美到人家喜宴都歡迎她穿;她還喜歡把秀髮留長,抹些花油,梳整乾淨,烏黑亮麗的,她覺得這是對自我的一種尊重。
可能母親窮慣了,家境見好後她向來對家人很大方。只不過我們母女倆,仍愛吃些能瞬間填飽肚皮的食糧。尤其刈包、餃子、肉包堪稱我三大摯愛,我喜歡它們都能撥開─就像人生處處充滿驚喜,你想的跟發生的全然不是同一回事。這類俗食凡物做得難吃當裹腹,要做得美味則暗藏內涵,細節裡全是功夫。
食材主角五花肉妙用其中,有多的脂肪還能煸豬油。我先前聽義大利友人說,他們餃子要夠黃,雞蛋加得夠多,才代表家境富裕;英國朋友則告訴我,過去貴族喜歡無瑕白糖,還請來侍僕專門手工切割,以顯尊貴。
我們家異曲同工,豬油用哪個部位煸也能見家底。豬腰部位是上選用在大菜,做給親朋好友看,豬肚部分拿去炸粿也沒人吃得出來;剛才說的五花肉來自肚腹,雖不是什麼高尚選擇,但我媽能將平凡化為神奇的廚藝,這點不在話下。
說到底,面子有時得撐出來。1990年代每逢佳節,親友算來得勤,每當客人一坐下來,嘰哩呱啦聊個沒完。我便躲進桌底下,拿起剪刀剪報紙。這是自從我眼睛開始好轉,母親教我認字的方法;每天剪的字不大相同,今天剪「愛」,明日剪個「希望」,剪字拼句子,就這樣拼拼剪剪,我的閱讀與寫作能力,短時間就進步很多。
我們家的餐桌也越換越大桌,最後變成一張大玻璃圓桌。雖然弄得我一點隱私都沒有,但有那麼多朋友喜歡吃母親做的菜,大抵是因為她總是真誠地為深愛的家人朋友洗手作羹湯,並證明能將這世間最為粗暴的飽足,昇華至心靈的溫柔。
記憶裡,她會興致勃勃帶著我到菜市場尋訪,跟著肉販阿伯、菜攤阿姨抽絲剝繭,從飲食提煉對文化與人群的包容,敞開心胸,感受從餐饗傳遞出家的溫情與愛。她總說:「孩子,妳如何感受吃,便幾乎決定妳如何做人。」
這就是我與餐桌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