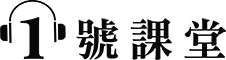為什麼我選擇去歐洲拜訪這些女人呢?實際上我所生長這片土地,有些根本的隱憂還懸而未決。我們這年代出生的孩子,父母大概都是這般:經歷童年艱辛,迎接臺灣經濟起飛時代,書讀得多的人少,發財的人卻很多。所以你可以想像父母對人生的解讀,以及所面對的現實,和我們這一代有多麼不一樣。
我知道我媽內心一直有夢的。她熱愛音樂,喜歡芭蕾;她能在任何地方跳起舞來。但她從沒真正實現夢想,她身處華人社會,不斷在父母、社會期待與自我價值之間拉扯,並且為了生存,她跟男人學習如何當個女人。我在這般社會環境裡長大,不是很能明白,為什麼我有了穩定工作,得以自力更生,卻無法打從心底感到快樂?這個社會讓我覺得一個女人她活得有沒有價值,不在於替自己付出多少努力,而是她已經這麼厲害了,但有沒有人要還是很重要。同時等著看她,在追逐自我成就的那天起,就必須犧牲另一塊至寶。
好多年了,臺灣都在談國際化,但是我總在職場與社會感到卑微,以致於我在他人文化面前,更是自卑的。你可以想見,我在充斥各種聲音的人生道路上,恐怕早已失去最簡單,為愛的人做道菜、好好坐下吃頓飯的動力。這種感覺很糟糕。我可以靠工作養活自己,但如若世界是一座森林,我基本上沒法覓食、生火與活下去。我開始察覺,如果我們沒有用雙手去創造些什麼,那將會失去內在最深層的自信。
我不得不說,前往歐洲的旅程,多半有名為「意外」的調味存在。這調味出現在臺灣公民投票選出第一位「女性總舖師」。在這個女性意識、自我價值、自我認同火侯高漲的時代;女人掌廚在公私領域彷若有了討論空間,可空氣中,卻瀰漫著絢爛炮竹燃燒完後的煙硝味。
這時代看似進步了。但桌面下,華人特有的性別權力關係,仍暗潮洶湧;幾萬年前就定下的睪丸素,仍讓一些除了體力也拿不出其他證據能好好活著的男人自命不凡;我也還在面對親友的結婚傳喚,那些話題總是不離年屆30,就該找個對象嫁了,事業再忙最後還不是得回歸家庭,女人就該這樣。
哪樣?我想起母親大半時光都待在廚房。我因為喜歡她做的菜,就以為她愛做菜;可是那熱油燙疤的手臂、高溫熾出的大汗,拼命刷洗鍋具的背影,猝不及防以一道火光從思緒裡迸出,燦亮地指引我必須去了解成長過程中,和母親一同揉饅頭的廚房,作為女性那窄小的飲食世界觀,究竟還有多少空間去伸展?我也意識到若想找到答案,我可能需要匍匐深穴,找到那把火,去親身經歷女性轉化身分的地方,並重新找回蹲在灶爐前的勇氣。
這趟旅程,無非是透過人類共通語言:飲食,尋找這世界是否還有另一群女性,與我們同行;另闢蹊徑所要找尋的也並非是新女性的表率,而是舊女性因應時代的演化族群。
在此基礎上,我的目的不是去強化女權,甚至我還想避免它遭到濫用。你或許會問:「那為什麼要只寫女人?」確實,我們可以沒有性別去討論身為人該享有創造幸福的權利,創造地點也未必盡在廚房。但我特別著墨女性,在於女人在這世界上,委實需要換個方式去發聲,若想獲得尊重,也還有長路要走。到頭來,我就想要親自去看,那把象徵知情識趣、推動文明自主的火源究竟在哪?它又如何烈火燄燄,讓自覺熬進我們骨子裡,並重新點燃我們對人們的尊重與對生活的熱情。當我們要去談新女性的時候,不可避免要談舊女性的存在。
回首前程,我承認自己起初認為:每個女人只要走出去,就勢必得擺脫渾身油煙的過去。你說不上來,在我從政治系畢業沒多久,社會便瀰漫一股從「吃什麼」走向「如何吃」的氛圍。大夥要麼把寂寞當品味,走進餐廳,安慰身心俱疲的腸胃;要麼煮出生活調劑,家中堆滿食譜,以證明人生諸多身不由己,我們至少都還能料理自己。
反觀我,身為一個完全不懂得做菜的女人。我內心對保守力量的反感,有點超乎自身想像﹔雖然我有些懷念母親家宴的精采,何以成為鄰里間的美談;她從不計較朋友有否帶了伴手禮,也未曾算計過投資報酬率。我想她對於烹飪是這麼一言以蔽之的─「那是你得吃飽,還想吃好的事。」但永遠做不出比老媽更美味的佳餚,也讓我對自己很唾棄。
尤其愛情專家不是聲稱:「要抓住一個男人的心,要先抓住他的胃」?我認為地球上至少有一半的女性能向妳證明:抓住男人的胃,不在於妳有什麼拿手好菜,最根本是妳到底是不是他的菜。
追根究柢,「女人進得了廚房,上得了廳堂」諸如此類被合理化的集體信念,誘發我內心的小抗拒,我抗拒的不是自己為何生而為女性,而是整體文化構築的女性價值。所以不難想像「女性們,共體時艱」是起初我來到歐洲的濫觴,我以為來到法國就能尋見新女性的涅槃,隨那優雅從容的行者,什麼都不在乎地抽根捲煙,自在人間。
可當我遊歷西歐、北歐拜訪12 位女性,這中間存在著太多變數。我睡過垃圾車也賣過藝、鏟過牛屎也趕過牛羊,自己都狼狽地難以想像,又何以盼尋那些坐在餐桌旁漂漂亮亮的華麗貴婦,逐而轉往探索真實火窯邊的濃情世故。
遇見這群女主人多半出乎我計畫之外,從法國、丹麥、英國、義大利到西班牙,她們年齡從32 到70 歲,近乎橫跨半世紀。每個人像似繳了塊人生拼圖,讓我把它們合起來,讓故事飄洋過海來到你面前,打開來,那是一幅深沈啟發的女性覺觀。
我只能概括地說,歐盟成立30 年以來的女性思辨,大致呼應了歐陸當代的飲食思潮─從獨樹一幟走向不拘一格:人們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色同時,培養與他人融合的本事,並企圖活得多采多姿。
這是個新舊女性難以壁壘分明的時代。任何人都無法拿自身民族觀點,去合理化任何一方的女性價值─哪怕這是顯而易見的思維誤區。我於是決定住進她們家裡,以這樣的方式拜訪歐洲女主人,讓她們用自己的生活樣態來說故事。這12 位女性在受訪過程中,時而感性又時而尖銳地分析自己,讓我足以記錄珍貴歐陸女性特寫,讓我們由此借鏡,開拓自身視野。
其中最重要的思考關鍵,便是我們總將焦點放在歐陸女人是什麼模樣,卻忽略了她們蛻變的進程。而一個國家烹飪藝術的璀燦程度,也大半和她是否經歷殖民歷史、披沙揀金他國飲食文化息息相關。到頭來,新女性是建立在多元民族融合的滋養上,影響她腦袋瓜最重要的蛋白質叫做知識。這些歐陸女主人便是要談─女人如何從多重角色與文化構築裡,走出傳統廚房,擺脫為家人奉獻而存在、為符合社會期待而偽善,進而尋見自身道路的故事。
接下來,我們所論及的烹調非僅限於菜餚,而是普羅大眾追求在生活裡保有質樸的尊嚴與自我的滋味。我也在這一路不斷反思出發的動機,挖掘女性在這世上真實存在的意義:用自身卓越與發光發熱,讓妳的同類感到她並不孤單。這個階段的我,也感受到母親帶給我的回憶,唯有妳重新去烹調它,才能死灰復燃。